谢荣雅是第一个拿下德国的iF,Red Dot,美国的IDEA以及日本的G-Mark四大国际设计奖金奖的华人设计师,可他却再也不想做工业设计师了,他要做“人类的观察家”。
谢荣雅变了。三年前,当他同时拿下iF,Red Dot(红点)和IDEA三项金奖时,世人都认为他经过苦苦努力终于攀登上了最高峰,可以在山顶振臂高呼了。可他自己却说,好像是一个人在沙漠里行走,以为绿洲就在越过山的另一头。好不容易站到沙漠的最高点时,才发现根本没有绿洲。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
而今天的他自信满满,谈到正在进行的新项目是研究一种涂料,涂在墙壁上自己能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仿佛他是一个百变的魔术师。我相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科技发展的速度永远要超出人类理解的速度。谢荣雅创办的大可意念公司在两年前开始与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人类5年之后甚至更远时会使用的产品。而他自己也已经幸运地从一个工业设计师成功转型为一个综合的、跨界的观察家。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台湾整个设计产业的转轨。
天生的跨界者喜欢画画却上了工科专业,与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谢荣雅也不得不走上这样一条“理所应当”的发展道路。毕业后,他有机会到宏做笔记本的设计工作。反正爸爸只知道他是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工作,至于具体做什么并不知情也不关心。谢荣雅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设计梦想。不过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工科背景,对材质的敏感,对工艺流程的了解,才使得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左右脑并用的成功的工业设计家。
而当谢荣雅读了商科研究生之后,又比其他工业设计师多了几分商业意识。从客户端考虑问题,使得他成为设计界中的一个异类。当别的设计师都把图纸画得精美绝伦时,他却只用5分钟画一个草图。因为他知道,图画得再漂亮,如果不能变成有形的产品,或者说在转变成产品的时候打了折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看的是销售结果,而不只是让客户满意。我得让‘顾客的顾客’满意才算成功。”谢荣雅总是从终端往回考虑自己的设计。比如他2008年得红点奖的作品,是一个可以放在口袋里的婴儿磅秤。把它从口袋里拿出后充气,把婴儿放上去,里面的气体会感受到压力的变化。这个产品并非高科技,但却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欧洲,很多护士要到宝宝家里去测量体重,原本要带一个很大的包,现在一个小小的口袋就可以了。
后来谢荣雅自己总结,能够实现从终端考虑问题,也跟自己独特的经营模式有关。从宏离开之后谢荣雅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接下第一个长期合约客户时就确定了一个模式,以“年度顾问”的方式而并非“个案”的方式。“谈个案,关心的是能不能结案,结案才能拿到钱。年度顾问的方式就不同,我要考虑的是,在一个会计年度里,我能帮客户创造多少价值。”因此,谢荣雅与客户的合作方式始终都是比较深入和长久的。
能够拥有设计的天赋,有工科的背景,又有商业的直觉,他已经是设计界中的佼佼者了。但是,对于谢荣雅来说,这些都不能使他满足,在经历了低谷之后,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痛苦的蜕变
为什么谢荣雅三年前拿到三项金奖时,却说自己不想从事设计了?这要放到台湾整个设计的大环境里来考量。
二三十年来,台湾大力发展3C产业,因为长期做OEM,电子技术到哪里就做什么设计。产品经理讲话非常有分量。产品经理大多是要设计师做外观,设计师最终沦为“做外观的机器”。做传统产业的更惨,设计师变成“OEM中的OEM”,都穿制服上班,每天打卡。台湾的设计师很难得到客户的信赖。设计图透过3D效果,看起来非常好看,变模型时就会差一点,量产时更差,因为客户往往为了节约成本,模具的材料就用次料来替代。到了市场上就会节节败退。客户不信任设计师,设计师也越来越没有独立的思考。政府缺乏长远的产业规划,企业为了商业利益追求短期的效应,整个市场处于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中,使得设计师难以潜下心来。
在设计界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谢荣雅已经厌倦了这种短视的环境,即使是拿到国际奖项也并不能改变这种现状。另一方面,有放弃设计的念头,也跟他本身的性格及宗教信仰有关。笃信基督教的他,从最开始就认为,造物主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最棒的设计是什么?是小孩!是生命本体的感动,不是靠我们的脑力和才华能够实现的。”所以当谢荣雅拿下工业设计的最高荣誉时,他不禁开始反思,最好的作品都不是人类设计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设计?
不过近两年,台湾的设计环境比以往有所改观。随着台湾大力提倡产业的升级转型,再加上台湾的设计师频频在国际上拿奖,政府和企业都开始关注到这股力量。谢荣雅的思想又活跃了起来。工研院和大可意念的合作,让谢荣雅看见了政府愿意将产学研的力量整合起来,去做一些前瞻性的东西。他的想法加上工研院的合作机遇,成就了他的脱胎换骨。
坚守的底线
其实很早以前,谢荣雅的作品就反映了他对环境和人类的关怀。在台湾,很多建筑工地外都有铁皮围篱。而台湾的台风比较频繁,这种围篱经常倒地,割伤行人或车辆。谢荣雅则研究出一种看似琉璃材质,其实是由ABS塑料模块组合成的蓝绿色围篱。这种材料抗风压,易组装,不仅成本低,而且可回收利用。“这设计有无限可能性,基于安全性与对环境的友善,政府应该立法使用这项设计”,美国IDEA大奖的评审曾经这样评论。
转型之后的谢荣雅,目标清晰也乐观了许多,不过身上的压力也更重了。他坦言自己事业中最困难的时期,并不是创业初期,恰恰是现在。“因为现在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必须要牺牲很多案子。我们必须认定是对人类有价值的,但是很多产业思考的是获利。有些案子我就不能接。如果不能维持自己一贯的想法,那就干脆不要做了。”可是现在的他,要为一个47人的团队负责,还有来自传统产业的经营合伙人,他的这种做法能否取得所有人的认同?
谢荣雅表示,自己很幸运,大家都是认同这样一个理念才来到这家公司的。而他唯一的合伙人在传统产业里是做吊扇的。吊扇在整个制冷系统里,耗费的能量最少。家里如果有吊扇,冷气的温度可以降低两度。没想到这个曾经被看成是夕阳产业的产品,如今却在欧美市场上成为主流。所以在改变人类生活、降低能源损耗的这些根本理念上,管理层的沟通没有障碍。公司在与产业合作时,都会用这样一个主轴来与客户讨论。
时间拉回到十几年前,谢荣雅刚刚创业,客户还少得可怜。当时有一个客户是做喷水头的。在服务他的时候,谢荣雅发现,喷水头里面有一个轴心是铁做的,可是铁遇水会生锈。他问客户,为什么不把这个轴心改成不锈钢的。客户说:“你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放到卖场,消费者来买,冬天不怎么用,到了明年春天,铁就会生锈,他们就会再买一个。如果他用不坏,我怎么维持这么高的销售量?”从此,谢荣雅再也不接这个客户的单了。“我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去思考。”
也许对于谢荣雅来说,有些东西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Q+A
《东企》:为什么否认自己是“工业设计家”?
谢荣雅:我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说我是工业设计家,因为我并不认为“工业设计”这个名词还能够在将来的十年二十年后继续维持。现在中国内地还在努力地做好工业设计,传统的工业设计无非是在人体工学的部分,整个造型的美学,以及商业的考量上。但是对我来讲,这本来就是解决设计问题必备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形体以外那种无形的东西。它的影响更深远。
《东企》:听上去很玄妙。
谢荣雅:我简单举个例子,我们车子都会抛锚,车子抛锚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赶快拿一个三角立牌,拿到车子后面30米的地方,提醒路人。这是自保的动作。但是事实上在台湾,好几宗车祸发生的原因,不是车子故障被人撞到,而是在他拿三角立牌的过程中被撞。作为一个设计师,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设计一个更漂亮的三角立牌,而是如何能避免他下车,因为下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最好在故障的过程中,能够在他的后方虚拟投影一个立牌,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实体的东西,能够自动跑到他后方30米。这是在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而不是造型设计的问题。在面对下一个阶段时,必须要抛掉工业设计这个名字,因为世界的未来并不为它所主导,世界的未来被一群能够解决更高层次问题的人所主导。
《东企》:从一个工业设计家转型成为一个人类生活的观察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思维的转变的?
谢荣雅:大概是在两三年前。2006年初,我已经知道自己同时拿到了三项金奖,我就开始思考,下一步是什么?工业设计的最高荣誉已经拿下了,再来挑战的就是自我。我一直在想,工业设计真的对人类有益吗?在很多时候,这个事情是对人类有害的。这是面临否定自己的阶段。我为什么要当一个工业设计师?我要怎么利用原有的能量做出对人类有益的事情?我两年前提出一个论证。我面对每一个设计时都要去问,为何需要设计?我认为最好的设计是不要设计。设计会造成污染。全世界最美好的东西都不是人类设计的。你认为一朵玫瑰花很好,很抱歉不是人类设计的。人类怎样设计都无法赢过全世界本来就美好的东西。树你种就好了,用来乘凉,为何要建造凉亭?要耗费多少能量?产生多少二氧化碳?我会面对否定自己、甚至否定设计的阶段。
《东企》:后来又是怎么找到出路呢?
谢荣雅:刚好在那个时候,工研院院长来找大可意念搞合作。所以我也必须要感谢,我们有机会与一流的研发团队合作。工研院的性质跟一般的产业界不太一样,一般的产业大部分考量的都是产品,半年之后要推出的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设计考量是比较商业的,工研院不一样,它担负着某些使命,尤其是台湾的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IT产业,这些部分是国家的综合策略。它是在做一些前瞻性的工作。比如说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世界是什么样的,人类究竟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团队是用来接轨到应用端。现在我有一半时间进行的都是面对地球暖化提出的解决策略,这远比做一个有形的产品对人类的影响更大。
《东企》:能否举个例子?
谢荣雅:现在台湾和大陆都在太阳能电池板这一块发展得相当好,我想要做些改变。未来的太阳能发电,将不需要现在所说的多晶硅、单晶硅,我可以直接用玻璃、塑胶的材料,这就不会改变人类现有的面貌。现在挂太阳能板,它会破坏整个都市的景观。这个事情就像纽约市长说要在帝国大厦挂一个巨大的风车,用来发电。出发点很好,但这会破环城市环境。你会发现,环保的议题常常会跟美学的议题形成矛盾。我要做的是,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要加入科技的成分,在美学的成分里带有科技对人类改善的行为。我们没谈市场。当你用美来解决科技,当它促成这样一个手段发生时,也就代表无限的商业机会。
《东企》:做一个整合者?
谢荣雅:对。这也是我对台湾能产生国际品牌的信心来源。当今各个生活的领域,都被国际大品牌把持,法国有服装,北欧有银器,这些品牌发展了几百年,我们不能与之抗衡。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把科技加进来如何?这一点是台湾有的优势。我在几年前设计一个作品,很简单,是一个包。但是这个包的材料很特别,是E-Paper(电子纸),这个包随时可以改变它的图腾。这是欧美公司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科技来当作发展的背景。但是这一点台湾有啊,大陆未来也可能有啊。我们有先进的科技能够落实在生活中。全世界70%的笔记本电脑都是两岸做出来的。
而我们拥有的这个东西,如果再结合传统文化上的认知,累积的遗产,包括手工的精巧,我们有机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品牌。在台湾我们也不断做这个事情,把新的材料放到笔记本上,比如竹片。把东方的中国的意向图腾甚至哲学的部分,老子的想法,把它融到这里面。我之前还有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太极球,太极的图腾立体的球,这个球就是小朋友的玩具,有趣的是,他玩这个球时就好像打太极拳一样。这个东西欧洲人设计不出来的。我渐渐看到这一块,用我们文化的优势赢过他们。
我本来还没有这样一个自信,直到从2003年开始我们不断在国际上拿奖,我感觉到我们的文化有优势。太极就是因势利导,这是西方人比较缺乏的观念,我们以前大禹治水是疏导的而不是围堵的。这是我们的哲理。就像我们正在研发的能产生光合作用的油漆,它不是在讲把森林砍掉盖房子,也不是说把房子拆掉建森林,而是在讲两者能不能兼容,能不能因势利导,寻求阴阳调和的折中点。至于商业利益这一段,自然是无限的。台湾的产业不断在追国外,为何不用老祖宗的思想一次就超过他们?我们在Red Dot拿下两项金奖,德国当地的企业都无法做到。
《东企》:为什么有信心能赢过他们?像德国,有发达的科技,也有先进的环保思想,优秀的设计师。
谢荣雅:这是个很有趣的议题,我和这个领域的朋友也会聊这个话题。奇怪,德国的科技是胜过我们的,比如汽车制造。为什么笔记本就做不过台湾?我们拥有什么优势?以前还不是看得很清楚。大概到了2000年时就明白了。因为那时了解到全世界大概70%、80%的笔记本都是台湾做的。我们发现非常奥妙的事情,他们做先进的科技研究可以,但是他们要整合成为应用的技术,能够符合成本、效能、品质的稳定以及生产作业量化,面对消费者市场的瞬息万变,弹性远不及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温州人为什么有钱?会抓机会。台湾也是,很小,都是中小企业,我们有很高的弹性和整合能力。这是我们近20年来经历的事情。
/ 東方企業家 孫揚
本文載自東方企業家 20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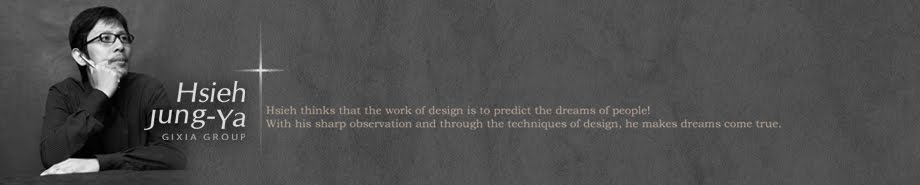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